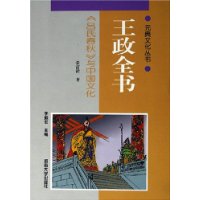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
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
作 者:张富祥 中国大陆
出 版 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丛 书:元典文化丛书
出版时间:2001年08月
定 价:26.00
I S B N :9787810417235
所属分类: 文学 > 诗歌词曲
标 签:国学 杂家 先秦哲学 中国哲学 哲学 文化研究 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 文化 综合 中国古代 诗歌词曲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介绍和讨论了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该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历来阅读它的人不算少,但又由于其文字艰涩,内容深奥,现代人极少再有人观顾它。本书正是出于此原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各位读者介绍并解读。全书以吕不韦的生平故事开篇。
目录
序 冯天瑜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
本书引言
一 吕不韦
二 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
三 “十二月纪”:上古王政的年历
四 天道观·发展观·历史观
1.《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和“天命”观
2.《吕氏春秋》的变易发展观和历史观
五 尚贤传统与“无为”政治
1.《吕氏春秋》论尚贤
2.《吕氏春秋》论“无为”政治
六 性理之说与帝王修身
七 礼乐文化与儒的功用
1.《吕氏春秋》与礼乐文化
2.论乐八篇
3.《吕氏春秋》对儒学的汲纳
4.“十际”之说及其他
八 民本思想与法的折衷
1.《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
2.《吕氏春秋》与法家学说
3.“尊君”问题
九 墨与名的吸收和批判
1.《吕氏春秋》对墨家学说的吸收
2.《吕氏春秋》对名家的批判
十 论兵八篇
十一 农学四篇
2.论土地的利用
3.论种植
4.论农时
十二 《吕氏春秋》的文化史价值
1.古典王官文化与先秦诸子
2.《吕氏春秋》与诸子的关系
3.王政理想与大——统政治
4.《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附录一 《吕氏春秋》选译
孟春纪 本 生 贵 公 情 欲
尽 数 论 人 孟夏纪 劝 学
尊 师 大 乐 孟秋纪 荡 兵
顺 民 仲冬纪 当 务 有始览
务 本 孝行览 下 贤 贵 因
察 今 审分览 任 数 用 民
为 欲 恃君览 长 利 爱 类
贵直论 贵 当 士容论 上 农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书摘
“我能扩大您的门庭。”
异人不解,说:“您不扩大自己的门庭,何必多管闲事来扩大我的门庭?”
不韦说:“您不知道,我的门庭要靠您的门庭来扩大。”
异人好像明白了什么,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让坐与他谈话。不韦乘机进说:“昭王老了,现在安国君为太子。我听说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但能为太子立嫡嗣(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正妻之子方可继承王位)。我能帮助您回国,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您为嫡嗣。”
这项交易一拍即合,异人甚至答应事成之后,与不韦共分秦国。据说吕不韦一面供给异人钱财,让他倾力结交宾客,树立自己的名誉;一面打点珍宝等物,入秦为异人游说。他首先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一说是其弟阳泉君)向华阳夫人进言,作为晋见华阳夫人的阶梯。及被召见,又添油加醋地说异人如何孝悌贤智,视华阳夫人为生母,虽在赵国为人质,还是日夜涕泣,思念着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自己不曾生儿子,本亦担心色衰爱弛,废立难测,经吕不书一番游说,终于同意把异人收为自己的儿子,并为之改名楚,使吕不韦为师傅。华阳夫人原为楚女,故为异人改名楚,后来史籍多称之为子楚,是为秦始皇父亲的正名。随后,华阳夫人通过枕边风,使太子安国君答应立子楚为嫡嗣,并刻玉符为信。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秦将王龄围攻赵都邯郸时,赵人欲杀子楚,子楚用吕不韦之计,逃归秦国。
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昭王死去,太子柱继位。这时柱已经53岁,第二年就发病死了,是为孝文王。接着是子楚名正言顺地继位,吕不韦由师傅被委任为相国,封文信侯,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航程。子楚这年30岁,按说正当年富力强,不料在位仅3年,也于公元前247年死去,谥称庄襄王。他的儿子政(也写作“正”)继承王位,时年13岁,即后来所称秦始皇。
秦王政的真实血缘身份,现在不大好考究了。传说吕不韦还在政治投机之始,就在子楚将来的继承人问题上做了手脚:他先是娶了一位绝对美丽而又善长歌舞的邯郸女子(一说为赵国豪家女,又称赵姬),使她怀孕,然后把她献给子楚——这暗度陈仓而生下的孩子便是后来的秦王政。政出生在赵国,当他父亲子楚逃回秦国时,他和母亲未得脱身随父逃走,幸亏被人藏匿了起来,才得以活命。其时他两岁多,从此就随母亲姓赵氏。直到秦孝文王时,子楚被正式立为太子,母子俩才被赵人送还秦国,从此政亦改从秦王室本姓,史称嬴政。
赢政即位后,吕不韦继续担任相国,并被赢政尊称为“仲父”。这“仲父”的称呼,原是对父辈的尊称,因齐桓公对帮助他夺取王位和称霸诸侯的管仲曾称“仲父”,所以嬴政对吕不韦也用了此称。吕不韦自担任相国时起,就继续奉行秦昭王东扩的策略,曾协助庄襄王命大将蒙骛攻占韩国的成皋、荥阳之地,设置了三川郡(在今黄河、洛河、伊河之间);又攻取赵国的上党、榆次等37城,设置了太原郡。不过在进攻魏国时,被魏国上将军、信陵君公子无忌联合五国兵打败了。吕氏的封邑,开始有蓝田(今属陕西)的12个县和河南洛阳的10万户,后来又包括了燕国献给秦国的河间10座城(在今河北献县一带),并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干人,一时莫比。
不过吕不韦在与王室的关系上也有隐忧,就是他和赵姬的关系。赵姬在庄襄王即位后,被立为王后;及秦王政即位,她自然又成为太后。照传说所言,吕不韦在攫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始终与这位赵姬保持着私通关系。然而在她成为太后之后,吕不韦不能不有所顾忌,时时担心与太后的私通会毁坏自己的前程。于是他又偷梁换柱,另找了一位“大阴人”缪毒做替身,使他假充宦官进入后宫,以满足太后的淫欲。其不知这一举动,恰恰埋下了他在日后宫廷斗争中失势的祸根。
相传这位年不满30的太后“绝爱”缪妻,为此她不得不付出作为一个女人虽不情愿却又不可避免的代价——先后两次怀孕生子。为遮人耳目,她在远离都城咸阳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建了别宫,时时出居。缪寡常为贴身侍从,得赏赐无数,家资暴涨,羽翼渐丰。到秦王政八年(前239年),这位假宦者竟被封为长信侯,不但领有在山阳(今河南焦作东)的采邑,而且有太原郡作为封国,凡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一应具物,任其铺张挥霍。他还借助太后控制朝政,事无大小,皆得参决,成为秦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此时嫪毐有家僮数千、宾客千余,太后集团与吕氏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显现出来。
人所共知,史称“蜂准(马鞍鼻)、长目、挚鸟膺(鸡胸)、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的秦王政,原不是可以任人玩弄于掌股之间的傀儡君王。公元前238年,即当他22岁时,他正式接受加冕典礼,戴冠佩剑,亲理政务,从此便一改“居约”之态,开始借机对缪、吕两党进行打击。其时有人告发嫪毐不是宦官,常与太后私通,有私生子二人,都藏匿私养,外人不知。缪毒得知自己的丑事败露,竟利用秦王政去蕲年宫(在今陕西凤翔)加冕之机,抢先在秦都咸阳发动暴乱,欲进攻蕲年宫。秦王政得知嫪毒叛乱的消息,马上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平叛,一举消灭了缪毐集团的所有实力,屠其三族,并杀太后所生二子;又下令太后迁出咸阳,使她幽居于雍城,不准再干预朝政。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中,依附于缪毐的卫尉、内史、左弋、中大夫令等高官,有20余人被枭首车裂;缪毒的舍人亦几乎全被削除爵位,流放到蜀地充军,只有少数牵连较轻的被罚为了徒。事情闹大了,一向号称“仲父”的吕不韦,这时显然也脱不了干系。不过秦王政当时并没有触动他,直到第二年十月才免去了他的相国职务,而仍然保留着他的文信侯爵位。此后,有一位在秦国为客卿的齐人茅焦,以母子之情说服秦王政迎回太后,仍使她居住在咸阳甘泉宫。为了防止吕不韦再与太后私下交往,秦王政下令吕不韦以文信侯身份出居他在洛阳的封国。接着又下令遍搜于国中,大规模地驱逐在秦国的各国游士,只是因李斯的上书劝谏才停止下来。
当时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吕不韦在各诸侯国中还有着相当的威望,因此在他出居河南的——年多时间里,各国派往秦国请求赦免其罪的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秦王政恐怕发生变故,于是在公元前235年下令吕不韦及其家属一并迁往蜀地。吕不韦接令,自度穷途末路,早晚不免被诛戮,遂喝下鸩羽毒酒自杀。他的死,最终结束了秦国历史上从昭王去世到秦王政亲政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
原始道家对“道”的解释本来就内容不一。有一种看法认为,《老子》书中的“道”是统摄“气”与“理”的,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等等,即隐约表达了一种气化生成的宇宙论观点。不过《老子》书中还没有直接提出“精气”之说。《吕氏春秋》所称的“道”或“太一”的本体究竟是什么,书中也没有明确的诠释,但联系有关论述来看,所指可能就是摄取于《易传》的“精气”。如《圜道》篇解释“天阅地方”,便以“精气一上一下”、“万物殊类殊形”为言(详见后)。
《尽数》篇更明确指出: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欤),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良);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直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之,因走而行之,因姜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类似的沦说所展示的是一种天道自然观,和《易传》及《管子》四篇一样,都是与传统的神学世界观格格不入的。这样的观念,实际在“十二月纪”本文中便有多方面的反映,只是尚未有专门的理论解释。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吕氏春秋》论及“鬼神”之事,也只是把它看成“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东西,几乎全不见称举人格神。传说孔子、墨子治学,“昼日讽诵习业,夜(梦)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
《博志》篇记此而强调指出: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高诱注云:“史曰日精所学,致无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此亦《礼记》以精巧圣智为“鬼神”之意。
《吕氏春秋·观表》篇说: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面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
这是说“先知”的“圣人”之所以超过常人,仅在于他们能够审知事物发展变化的表征,并由此总结出“不得不然”的规律而至于“道”而已,并无什么神秘可言;常人不至于“道”,或以为“神”,或以为“幸”(偶然),其实非“神”非“幸”,偶然中包含有必然。所以,《吕氏春秋》对于卜筮之类媒介人神的工具也持否定的态度。如《尽数》篇说:“今世上(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察贤》篇说:“今夫塞(赛)者,勇力、时日、卜筮祷无事焉,善者必胜。”《明理》篇则历举种种大妖、人妖、物妖之祸,以说明妖祸之兴皆由于人事之不善。《慎大览》记有一个故事:
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你们国家)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这假托的故事自然不能出于周初,却也把春秋以来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倾向揭示得非常明白。《疑似》篇还有个不怕鬼的故事,也可借以说明《吕氏春秋》不迷信鬼神的倾向。这故事说:有个乡下老人去赶市,喝醉了酒。归途中,“黎丘之鬼”扮成他儿子的模样扶他走道,百般折磨他。老人回到家,大骂儿子:“我做父亲的哪点对你不好,为什么我喝醉了,你在路上折磨我?”儿子不知怎么回事,跪在地上哭泣说:“真是作孽,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到东村借债去了,您可以去问一问。”老人相信了,就说:“一定是那个奇鬼捣乱,我曾听说有这样的事。明天我再去喝酒,要是碰上奇鬼,一定刺杀它。”第二天一大早,老人又到市上,大醉而归。他儿子怕他回不来,就去迎他,不料老人望见真儿子,以为是鬼,拔剑而刺之,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这故事自然是说,“鬼”很会迷惑人。但老人的精神还是可敬的,说明早在数千年前,中国人已经不那么迷信“鬼”了。当然,《吕氏春秋》对鬼神的否定是不彻底的,在谈及阴阳失次、四日寸异节的妖祸怪异时也还有不少迷信的成分。
在古代天道观的思想链条上,“天命”观念是重要的一环;原始儒家对待这一问题,一向采取两分的立场和务实的态度。例如在孔子那里,便一面承认“天命”的存在,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张君子“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一面又强调“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怨天,不尤人”,面对现实乐观豁达,摒除空言,重视实干,力求尽人事以应天命,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吕氏春秋·知分》篇对此亦有集中的论说,并且主题即是“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的终极关怀,而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篇中所举的例证之一是:大禹巡视南方,过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皆大惊失色,举措无主。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结果黄龙俯首低尾而逝去。作者因此发论道:
禹达手死生之分、利害之经也。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味废伏,有盛盈岔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愉)然而以待耳。
……